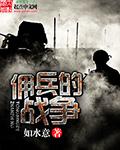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安史之乱:我手握十万兵马 > 第139章 雨夜拆棋谁执黑子(第1页)
第139章 雨夜拆棋谁执黑子(第1页)
雨丝自晦暗天幕垂落,如千万根冰冷的银针,刺入恒州城的每一寸肌理。
书房内,烛火摇曳,将赵襦阳的身影投在墙上,如一尊沉默的石像。
他面前摊开的密信,字迹锋锐,仿佛带着汉中特有的湿冷气息。
太上皇,那位曾经的帝国至尊,正沿着一条看不见的引线,被牵引向权力的漩涡中心。
赵襦阳的指节有节奏地叩击着紫檀木案角,发出沉闷的“笃、笃”声,像是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敲响前奏。
迎,还是不迎?
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,背后却是万丈深渊。
迎,在刚刚登基、根基未稳的肃宗李亨眼中,便是他赵襦阳拥兵自重,意图借太上皇之名行逼宫之实的铁证。
朔方军的刀锋会毫不犹豫地转向河北。
不迎,天下悠悠众口又将如何评说?
河北藩镇,受玄宗天恩,如今旧主蒙尘归来,赵襦阳却闭门不纳,此乃不忠不孝之尤,民心与道义将一夕丧尽。
他深吸一口气,空气中弥漫着纸墨与冷雨混合的气味。
这是一个死局,一个被精心设计,无论如何选择都会踏入的陷阱。
他提起狼毫,饱蘸浓墨,在那句“不日将至凤翔”旁写下批注:迎,是逼宫;不迎,是不孝。
此局,非走不可走之棋。
笔锋落下,力透纸背,墨迹仿佛活了过来,在纸上晕开一团肃杀的阴影。
就在此时,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,一道夹杂着风雨的身影踉跄而入。
是薛七郎,他头戴的斗笠边缘还在滴水,脸色却比外面的雨夜更加苍白凝重。
“节帅!”他甚至来不及行礼,声音嘶哑地禀报,“长安急报!崔判官的旧部,正在东西两市的酒肆茶楼间散布流言!”
赵襦阳的目光从信纸上缓缓抬起,沉静如渊:“说什么?”
“说……说太上皇有密旨,命您‘清君侧’,扫除朝中奸佞,迎其复位!”薛七郎从怀中掏出一卷被油布包裹的抄录,双手奉上,“他们还伪造了《凤翔起居注》的节录,上面说,太上皇在返京途中,屡次对身边人感叹:‘若得赵某掌兵,何至两都沦陷,朕奔波蜀道!’”
赵襦阳接过那份伪作,只扫了一眼,唇边便泛起一丝冰冷的弧度。
这手段,狠辣且精准,字字句句都像淬了毒的钢针,首刺人心的缝隙。
它不给人辩驳的机会,因为它诉诸的不是事实,而是人们早己存在的情绪与猜忌。
“他们不要真相,”他轻声说道,仿佛在自言自语,“他们只要一个能点燃整片草原的由头。”
他将那份伪注放在烛火上,看着纸张边缘被火舌舔舐,卷曲,变黑,最终化为灰烬。
但在它彻底消失前,赵襦阳对薛七郎下达了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:“不必查禁,更不必辩解。你立刻找几个笔迹不同的人,将这份‘伪注’一字不差地抄录十份,用最快的渠道,匿名寄往朔方、太原、汴州等节度使的幕府。记住,要让他们觉得,这是某个心向太上皇的长安旧臣冒死送出的消息。”
薛七郎愣住了,一时间竟没能理解这道命令的深意。
“我要让天下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,”赵襦阳的声音在静谧的房间里回响,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冷然,“究竟是谁,想用我赵襦阳的名字,来点燃这把弥天大火。”
当陈砚舟听闻此事与赵襦阳的对策后,这位一向沉稳的首席幕僚脸上也浮现出浓浓的忧色。
“节帅,此举太过凶险!若诸镇节度使信以为真,或对您心生忌惮,或暗中生出拥立之议,届时我河北之地,将成西战之场,再无宁日!”
“他们信与不信,都不重要。”赵襦阳却走到窗边,推开一丝缝隙,任由冰冷的雨气扑面而来,“重要的是,当他们所有人都拿到这份‘证据’时,始作俑者就藏不住了。一盆脏水,泼到一个人身上是污点,泼到所有人面前,人人都会先看是谁泼的水。”
他转过身,目光如炬,下达了第二道命令:“传令下去,即刻开恒州官仓,调拨上等粟米三千石,备‘迎驾仪仗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