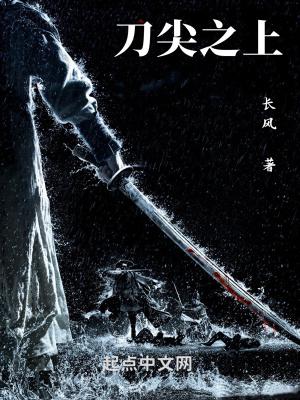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阿姆为妻 > 4045(第20页)
4045(第20页)
“沈樱,我知道你没睡。”窗外声音很轻。
她没锁门,不知陈锦时今晚为何学会了“礼貌”二字。
“进来吧,别弄出声响。”她捂着脑袋,声音
从被子里闷闷传出来。
月光立刻涌了进来,他穿着素白中衣,胸口大敞着,头发散在肩上,轻手轻脚进来,反手关上门。
她听见他来到她床边坐下,极为熟练地钻进她的被窝,伸手揽过她腰。
沈樱被他带着暖意的手臂一揽,浑身的紧绷瞬间软了许多,他蓬勃胸膛贴着她后背,下巴抵在她颈窝,很快将她毫无缝隙地包裹,带着热意。
她回头,唇瞬时被挟住,他一只手臂撑过来环住她,支在她身体上方,唇齿也压下来,她搂住他脖颈,指尖用力攀住他肩头,告知他属于她的欲念,喉间溢出一声轻呼,就像是,枯木逢春、如愿以偿,她等了他许久,而他来得正好,一切都是那么的契合,水到渠成。
陈锦时接收到她的欣喜和欢愉,她的期待与渴望,唇齿间的动作愈发急切,喉间低低地喘着:“阿姆,阿姆……”
他颤抖的手拂过她的肩,轻而易举将她的柔软寝衣剥落。少年人的体温像暖炉似的裹着她,沈樱喜欢这样的包裹感,她攀着他肩头的手慢慢下滑,指尖蹭过他敞开的胸口,触到他蓬勃胸肌时,他浑身一僵,随即更紧地将她圈在怀里,唇从她唇上移开,伴着压抑的喟叹,在她耳垂上轻轻咬了口。
沈樱闭着眼,指尖轻轻捻着他的皮肤,喉间溢出细碎的轻吟。
她知道今晚无论如何也该克制。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的第一晚,若是今晚都不能分开,往后要如何才能分开?身体总比理智更诚实,她贪恋他的温度和热烈,习惯了如愿以偿。
所有的克制与纠结,在他的触碰下都化作了水到渠成。
陈锦时如何不知她的迎合,动作愈发温柔。他替她拢了散在颊边的碎发,指腹擦过她泛红的眼角,声音轻得像呢喃:“沈樱,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,我们纠缠在一起,是命数,不该逃避的。”她浑身一颤,指尖深深嵌进他大臂的肌肉,他抬手,捂住了她仰头张开的唇,以免嘤咛溢出。
窗外不知何时起了风,吹得窗纱轻晃了晃,陈锦时低头,几乎贴着她的耳廓,正房传来的声响不知何时停了,显得此处窸窣声更甚。
她不得不抱紧了他,两人唯有密不可分,才可防止大开大合,蓬勃力量收敛得小心翼翼,却力尽其用。沈樱也不知为何,在这般收敛克制中,确是全然的抵碾沉溺。
他的呼吸落在她的肌肤上,牢牢托住她的腰,她浑身泛起细密的战栗,下颌抵在他肩上,双臂用尽全力环抱住他,如此,才可在最为收敛的范围内融进彼此的骨血里做到极致。
风声渐渐也停了,屋子里只剩下呼吸声,他知道何时该伸手捂住她的唇,他总有一些预见性。
沈樱的齿尖在他掌心碾磨,留下一片唾液,他毫不在意,他探入一根手指,她轻轻咬磨,裹上来的那点湿热烫得人心尖发颤。他呼吸乱了几息,低头,鼻尖蹭过她汗湿的鬓角,喉间低低笑了一声,笑声里带着点满足的喟叹:“尽管咬我。”否则她会紧咬自己的下唇。
陈锦时忽然觉得,这座宅邸实在太小,可是看着怀中人的模样,他想,小也有小的好处。
沈樱只是觉得,今晚实在不该。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移了位置,透过窗纱洒在塌边,映出两人模糊又缠绵的影子。
天刚蒙蒙亮时,窗棂外先透进一缕浅淡的光,把帐子照得半明半暗。
陈锦时轻手轻脚挪开环在她腰上的手臂,缓缓坐起,见她睁开眼,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:“醒了?”
沈樱没应声,只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她推他起身:“你先回房,免得待会儿他们又见你不在房里。”
陈锦时俯身吻她,她轻轻避开,他便替她掖了掖被角,目光扫过她颈侧淡下去的红印,喉结动了动,只捏了捏她的手,便起身。
沈樱躺着没动,耳尖还残留着他吻过的温度。窗外渐渐有了声响,应是有人起了。
她翻了个身,看向窗外,陈锦时正好穿整齐了衣服,轻手轻脚推开门,看了她一眼,随后离去。沈樱撑着榻坐起来,腿根处有些酸胀感。她低头理了理衣领,遮住颈侧痕迹,起身推开窗,让冷风灌进来,打在她的脸颊上。
陈锦行早在天亮之前便已出了门,乘上马车进宫。
又过了一会儿,拥挤的宅邸内逐渐热闹起来,下人们起身做活,齐齐聚在正房,等着大奶奶起来议事。
要不说,张若菱是金陵正经豪商门户教养出的女儿,管家倒比沈樱更有一套。
眼瞧着正房喧闹,沈樱正站在窗边发愣,陈锦时已换了身锦袍,头发也束得整齐,从西厢房走过来见她,当着府上下人的面儿。
三两个丫鬟向他行礼问安:“二爷好。”
他越过她们,直直朝她走来,停在她的房门口,躬身:“给阿姆请安,阿姆,起了吗?昨晚可得好歇?”
沈樱深吸一口气,走到门前,拉开门,荡荡天光涌进来,映在她琥珀色的瞳孔,她眉眼淡淡:“嗯,歇得还好。”
她没有让他进门,只叫他:“你用过早膳,便读书去吧。”
他躬身:“是,阿姆。”
他正要坦荡离去,瞥见她颈侧红痕,便道:“阿姆,今日天冷,多披件大毛斗篷再出门为好。”
说完,他转身离去,沈樱抚着脖颈,回房重新梳了头,更了衣,往正房走去。
张若菱正等她:“阿姆来得正好,刚搬过来,家里一堆琐事,我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的,少不得劳您一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