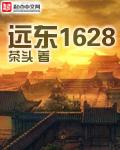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浮玉录 > 101墨痕虽薄掀学潮棠影沉静隐风雷(第1页)
101墨痕虽薄掀学潮棠影沉静隐风雷(第1页)
民国二十二年,五月。
《塘沽协定》的消息,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,烫在每一个北平人的心尖上。报纸上冰冷的条款——“划冀东为非武装区”——像一把钝刀,割断了北平与它最后的军事屏障。这座千年古都,一夜之间,成了赤裸裸暴露在日军刀锋下的“危城”。
贝满女中,墨痕社的活动室内,空气凝重。新任社长吴灼坐在窗边,沉静的面容比平日更显苍白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社刊清样的边缘。副社长林婉清则像一只被激怒的雀鸟,在房间里来回踱步,原本明媚的脸庞此刻涨得通红,语速又快又急:“丧权辱国!他们把华北的大门就这么敞开了!”她猛地停在桌前,看向吴灼,“灼灼,我们不能沉默!这期社刊,必须发出我们的声音!”
吴灼抬起头,目光缓缓扫过围拢过来的陈小芸、李英、小赵和刚入社的小刘。她深吸一口气,声音不高,却异常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,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庄重:“大家还记得,沉墨舟先生创办墨痕社的初衷吗?是希望我们以笔墨书写性灵,以思考探求真理。”她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与坚定,“如今,沉先生为求新知,已东渡留学。他曾说,墨痕之痕,贵在真诚,贵在敢言。”
她站起身,走到活动室前方那块沉先生留下的、略显陈旧的匾额下,手指轻轻拂过“墨痕”二字。“现在,国难当头,真理便是救国,性灵便是呐喊!沉先生虽不在社中,但墨痕社的精神火炬,不能因他的离开而熄灭,更不能在我们手中黯淡!我们要用我们的笔,将这精神传承下去,让它燃烧得更旺!让这墨痕,不仅留在纸上,更要刻进时代里,刻进每个有良知的国人心里!”
这番话,令社员们群情激奋。林婉清第一个响应,她用力点头,眼中燃着火焰:“对!灼灼说得对!沉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缩头,肯定失望!我们要做给他看,墨痕社的骨头是硬的!”
“社长,我们听你的!”
“对!我们不能让墨痕社无声无息!”陈小芸、李英等人也纷纷表态,刚才的犹豫被一种更崇高的使命感所取代。
吴灼看到大家重新凝聚起来的士气,点了点头,迅速开始分工,语气果断:“好!那我负责主笔社论和时评。婉清,你写檄文。小赵,负责所有对外联络和版面设计,你的点子多。李英,你心思缜密,负责资料核实。小芸,誊写的重任在你身上。小刘,地图的事交给你,务必醒目。”
林婉清眼睛亮得惊人,“我们是墨痕社,笔墨就是我们的武器!小芸,你的字最工整,誊写版面的重任就交给你了
,局》。她的文字,一如既往的冷静、缜密,引据充分,层层剖析,将协定背后的屈辱与未来的巨大危险,揭露得淋漓尽致,字里行间却蕴含着压抑的悲愤与力量,与她沉静的外表形成巨大反差。
而林婉清的文章则截然不同,标题就直接是《告全国同胞书》,开篇便是:“华北之大,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!”字句铿锵,情感奔放,如同战鼓,敲击着读者的心灵。她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“读者心声”栏目,鼓励社员和相熟的同学写下只言片语的感受,夹在社刊中散发。
活动室的灯火通明持续了数个夜晚。油印机嗡嗡作响,空气中弥漫着油墨和社员们汗水的味道。林婉清不时冒出“鬼点子”,而吴灼则沉稳地把握着大局,偶尔对林婉清过于大胆的想法予以修正。在吴灼的领导下,墨痕社这个小小的团体,如同一部精密的仪器,为共同的目标高效运转起来。
林婉清不时冒出“鬼点子”:“我们把特刊迭成小飞机怎么样?从教学楼窗户放出去!”“不行不行,太招摇了。诶,我们可以塞进图书馆热门书的书脊里!”
最终,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《墨痕·国难特刊》,通过林婉清那四通八达的“关系网”——她在燕京大学的表姐、在清华读书的远房表哥、甚至通过陈小芸、李英等人兄长故交之子在北大的人脉——如同秘密火种,被小心翼翼地送入了叁所顶尖学府。
效果是爆炸性的。
这本能源自女中学生之手的薄薄册子,以其不容置疑的事实、深刻的分析和喷薄而出的爱国热情,迅速在高校中引发了巨大共鸣。清华园的布告栏上,贴满了针对《塘沽协定》的抗议书,其中不少观点直接引用了吴灼的文章;未名湖畔的辩论会上,学生们激辩时局,林婉清那篇檄文中的句子被反复引用;就连燕京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,也拿着这本特刊,面色凝重地讨论着。
五月末,一场由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起,北大、燕京等校迅速响应的联合大游行,如同决堤的洪水,席卷了北平街头。数千名学生高举标语,高呼口号,“反对《塘沽协定》!”“保卫华北!”“收复失地!”的声浪震天动地。
游行当日,贝满女中课堂寂静。中学女生们虽无法走上街头,却都心系外界。下课铃一响,大家便涌向靠街的窗户,努力倾听那隐约传来的、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声浪。
吴灼和林婉清并肩站在走廊尽头。林婉清激动地抓着吴灼的手臂,眼眶湿润:“灼灼,你听!你听啊!我们的声音…没有被埋没!”
吴灼没有说话,
,的、纸张粗糙、封面素朴的册子。
“处座。”陈旻站定。
吴道时这才抬起眼,目光落在陈旻手中那本与书房格调格格不入的册子上,眉头几不可察地微蹙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