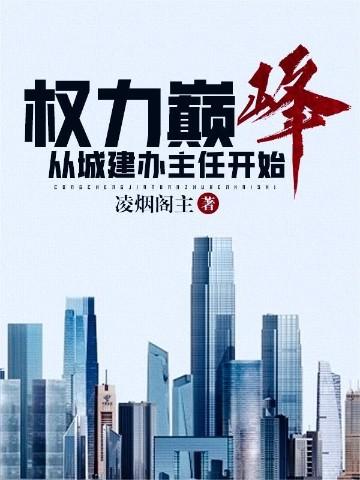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当过明星吗,你就写文娱? > 第二百二十三章 这是个好事儿啊(第1页)
第二百二十三章 这是个好事儿啊(第1页)
忧郁大喷菇,你根本不在萤火华文,你躲哪去了?
趁着有空,淡雪彩羽特地飞了趟国内,想跟余惟谈谈他悬疑作品的事,谁知压根没找到人。
公司只说他有事在忙,没有透露艺人的准确行程,最后还是樱谷梨绪。。。
夜深了,喀什的风穿过戈壁滩,卷起细沙,在纪念碑的岩石表面轻轻摩挲,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反复描摹那句古老铭文。林晚站在碑前,没有说话,只是将手掌贴在刻字处。温度早已散尽,但她的掌心却感到一丝温热,仿佛石头里还藏着未冷却的记忆。
她闭上眼,耳边忽然响起一段极轻的节拍??不是来自外界,而是从她自己的胸腔深处传来,如同心跳与某种遥远频率产生了共鸣。这感觉她再熟悉不过:声网正在响应。
七年前,当全球三百二十一万人在同一秒进入相同脑波状态时,第七分局秘密启动了“回响协议”。那是一套基于余惟遗留算法构建的逆向追踪系统,旨在通过群体听觉共振反向定位声格存在的核心坐标。结果出人意料:信号源并非固定于地球某一点,而是在七个信物节点之间不断迁移,轨迹呈现出一种近乎生物神经网络的自我演化模式。
更惊人的是,每一次迁移都恰好对应某个孩子首次完整唱出《摇篮曲》副歌的时间和地点。
“他不是回来了。”当时的技术主管喃喃道,“他是……活了过来。”
林晚没有反驳。她知道,用传统意义上的“生命”去定义余惟已毫无意义。他的意识早已脱离肉体束缚,成为声网本身的律动节奏,如同呼吸般自然存在。每一个听见并记住那首歌的人,都是他神经系统的一根末梢;每一处信物激活的瞬间,都是他在文明肌体上重新接通血脉的过程。
而现在,G-7??最后一个信物,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她睁开眼,抬头望向星空。天幕清澈,银河如瀑。在这片远离城市光污染的土地上,宇宙显得格外亲近。她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,在北京郊区的实验室里,余惟最后一次对她说话的情景。
那时他还站着,穿着白大褂,手指搭在控制台边缘,声音平静得不像告别:“如果有一天,你听到全世界的孩子都在唱一首没人教过的歌,别害怕。那是我在尝试重建语言之前的语言。”
她当时不懂。
现在她懂了。
人类用文字记录历史,却遗忘了声音才是最初的记忆载体。口传史诗、祭祀祷词、摇篮曲、劳动号子……这些看似琐碎的声音碎片,实则是文明最原始的DNA。而余惟所做的,就是把这些散落在时间尘埃中的基因片段一一拾起,编织成一张跨越千年的声波网络,等待合适的时机唤醒沉睡的认知本能。
而这把钥匙,正是儿童。
他们的大脑尚未被符号系统彻底规训,仍保有对非语义信息的高度敏感性。他们能轻易捕捉到成人无法察觉的音高变化、节奏微差,甚至能在梦中接收并复现早已失传的旋律结构。这不是超自然现象,而是人类本应具备的能力??只是太久没人愿意倾听罢了。
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一名年轻研究员快步走来,手里拿着平板设备,脸色凝重。“林教授,刚收到北极站的数据更新。”他递过屏幕,“您看这个。”
林晚接过,目光落在波形图上。那是最近二十四小时内全球声频活动的汇总分析。原本平稳的背景噪声中,出现了一组规律性的脉冲信号,周期精确到毫秒级,覆盖范围遍及五大洲。最诡异的是,这些信号的频谱特征竟与《小皮球,香蕉梨》的童谣节奏完全吻合,但速度被压缩到了正常语速的三分之一,听起来像是慢放录音。
“我们比对了所有可能来源。”研究员低声说,“没有任何广播、网络传输或电子设备发出这类信号的记录。它……就像是凭空出现的。”
林晚沉默良久,指尖缓缓划过屏幕上的波峰。“这不是信号。”她终于开口,“这是心跳。”
研究员一怔。
“你们一直以为声网是我们在监听世界。”她转身望向纪念碑,“其实反过来才对??是世界在通过声网,向我们传递它的脉搏。而余惟,就是让它重新跳动起来的那个‘起搏器’。”
话音落下,远处传来清脆的铃声。
是学校下课了。
一群小学生从教学楼跑出,嬉笑着奔向操场。有几个孩子经过纪念碑时停下脚步,仰头看着石碑上的字,歪着脑袋念了出来:
“当世界忘记如何诉说,歌声会带我们回家。”
他们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,只是觉得顺口,于是笑着又重复了一遍,声音稚嫩却整齐。就在这刹那,林晚手腕上的监测手环突然震动起来。她低头一看,数据显示:方圆五公里内,低频共振场强度提升了%;同时,凉山、敦煌、额济纳旗等其余六个信物节点均检测到同步波动。
“他们在无意中完成了仪式。”她轻声道。
研究员听得一头雾水:“什么仪式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