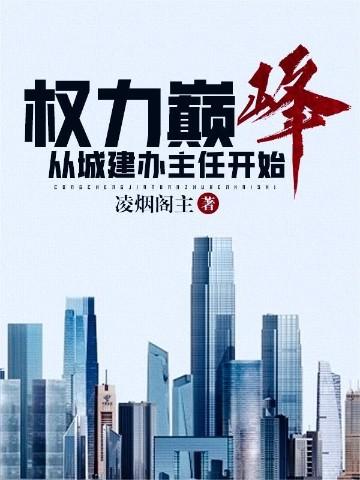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全家夺我军功,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> 第641章 本王不准你走(第1页)
第641章 本王不准你走(第1页)
秋夜雾色里,许靖央骑在马上,冷冷地看着平王。
她没有退让的意思,反而轻夹马腹,踏星又朝前两步。
“那我就要硬闯了,请王爷恕罪。”
话音刚落,附近黑暗的巷子里,传来整齐的拔刀声。
许靖央微微侧眸,月光所照不到的暗巷里,偶尔闪过刀刃的寒光。
她凤眸平静,毫无波澜。
听声音,不过几十人罢了。
还不等许靖央说话,就见平王冷声呵斥:“将兵器都收起来,怎么,你们打算被她杀穿么?还是说,有人有信心,能打得过昭武王?若。。。。。。
夜雨如织,檐下铜铃轻响,仿佛低语着未完的誓约。阿星坐在灯塔顶层的旧蒲团上,手中那支笔终于落了墨,在宣纸上缓缓铺开一行字:“守夜人不眠,因死者尚未安息。”
她搁下笔,望着窗外雨幕中的梅林。那些她亲手种下的树,如今已亭亭如盖,枝头缀满初绽的血色花瓣。雨水顺着叶片滑落,像无声的泪,又似血脉滴坠。昨夜她再度梦见母亲??不是年少时牵她手登塔的模样,而是披甲执刀、背影决绝地走向战场。风雪漫天,母亲回眸一笑,唇形分明说了两个字:**值得**。
这两个字,如钉入心。
她曾以为终结献祭便是救赎,可这几月来,各地传来的消息却让她明白,真正的黑暗从不在地宫深处,而在人心幽微之处。朝廷虽重修史册,追封英烈,但地方官吏仍暗中删改名录,将“叛族”者剔除;有些家族为保爵禄,竟谎报亲族战功,冒领抚恤;更有甚者,掘坟毁碑,只为湮灭真相。
而最令她心寒的是,有人开始称她为“逆女”。
“山长,”门外传来脚步声,是书院最小的弟子小禾,“京中信使到了,带来一封密函。”
阿星接过信,拆开,火漆印上刻着一只展翅的鹤??太子府的徽记。信纸泛黄,字迹潦草,显然仓促写就:
>“阿星姑娘:
>宫中风云骤变,帝疾加重,灵素一脉旧党欲借机翻案,诬你母当年弑姐夺权,拟削其追谥,废《英烈志》。我力保未成,恐诏书三日内即下。另闻北狄遣使求和,实则屯兵边境,意在窥伺内乱。危局将至,望速决。
>??李昭”
她看完,指尖微微发颤。
灵素……那个名字再次被提起,像一把锈钝的刀,割开早已结痂的伤口。她的姨母,被写成“叛族逆女”的女子,实则是千年来唯一试图打破献祭轮回的人。她偷走半卷《守夜录》,逃往北境,最终死于族中追杀。而今,那些靠谎言起家的权贵,竟要再次抹黑她,以此否定整个《英名录》的正当性。
阿星闭目良久,忽而起身,推开灯塔木门。风雨扑面而来,她却不避,任冷雨打湿衣衫。
“敲钟。”她说。
小禾愣住:“可是……集令钟从未在雨夜敲过。”
“正因从未有过,才该此刻响起。”阿星声音沉静,“去告诉所有人,明日辰时,讲堂议事。我要他们亲眼看见,历史如何被篡改,亲人如何被污名,而我们,该如何守住最后的光。”
钟声破雨而出,一声接一声,穿透迷蒙夜色。书院弟子纷纷披衣而出,无论老幼,皆持灯前来。讲堂内烛火通明,竹简堆叠如山,墙上挂着北境全图,红线标注的每一处,都是他们用脚走出来的真相。
阿星立于台前,手中捧着一只铁盒??那是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遗物,封存二十年,从未开启。今日,她当众取出钥匙,轻轻打开。
盒中无金无玉,只有一叠泛黄信笺、一枚断裂的玉簪、还有一本残破日记,封面写着:“灵素手记”。
她展开第一封信,声音清冷如霜:
“吾妹阿月,今夜我写下此信,知你未必能见。许昭之罪,不在外敌,而在宗庙之内。双生献祭非天命,乃权谋之具。历代‘守夜人’并非自愿赴死,而是被囚、被控、被炼化为星核养料。我亲眼见七十六名姐妹被活埋于归愿峰底,血肉滋养地脉……而族老们,却称她们为‘荣升’。”
堂下一片死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