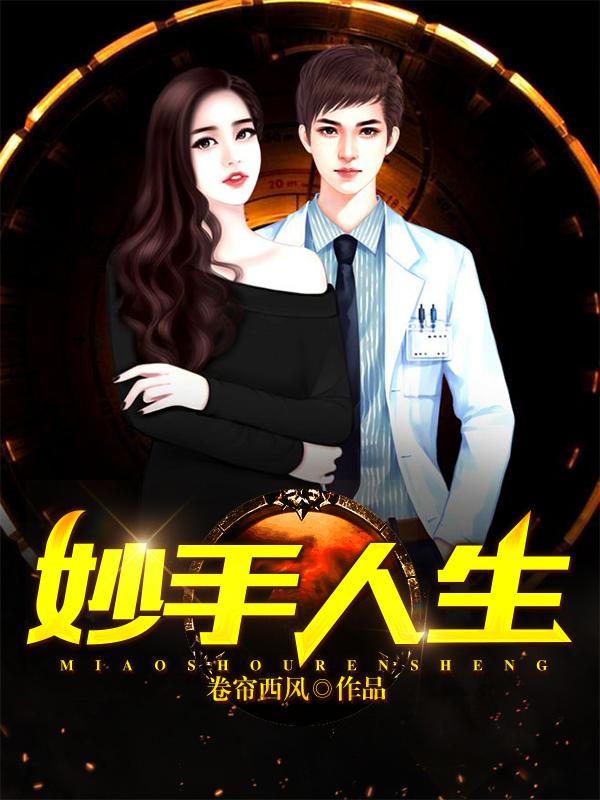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魏晋不服周 > 第196章 上桌吃席2(第2页)
第196章 上桌吃席2(第2页)
阿禾没有争辩。她在村口支起帐篷,夜里点燃油灯,开始朗读《治理律》第一章。起初无人理会,直到有个患肺病的老妇踉跄而来,哭诉儿子被豪强强征为奴,官府不理。阿禾翻开《人身保护权》条款,一字一句读给她听:“凡中华子民,不得非法拘禁,违者以重罪论处。”
老人颤抖着问:“这……这真能管用?”
“能。”阿禾坚定地说,“只要你敢说出来。”
第二天,她带着两名团员走访县衙,递上百姓联名申诉书。县令是个世家子弟,冷笑不止:“小小女子,也敢干预公务?滚出去!”
阿禾不退,只从怀中取出一枚铜牌??那是李知微临终前亲手授予沈云娘,后传至她的“民考合格证”,编号“零零一”。她将铜牌放在案上:“根据《监察法》第十七条,持此牌者,有权调阅地方政务记录,并接受民众投诉。你若不受理,请写下理由,我将呈报建康考绩院。”
县令脸色骤变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:一旦被查实“拒不履职”,不仅丢官,还将列入“失信名录”,子孙三代不得入仕。
三天后,被囚少年获释,豪强被立案调查。消息传开,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赶来。有人带着发霉的田契求助,有人抱着病儿求医,更多人只是想看看??这个敢跟县令对峙的小姑娘,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怕死。
阿禾一一接待。她不懂医术,便请随行女医诊治;不会丈量土地,就拿出测量尺现场教学;遇到复杂案件,她便组织村民召开“临时评议会”,让大家投票表决。十日后,村里自发成立了第一个“平民监督组”,推选两名老农、一名寡妇、一名退伍老兵为成员,负责监督粮仓与赋税。
临别那晚,村民们燃起篝火,围着她跳舞唱歌。一个七岁男孩怯生生递上一幅画:歪歪扭扭的房子里,坐着三个小孩,头顶写着“我要念书”。他小声说:“姐姐,你能留下来教我们吗?”
阿禾眼眶发热。她蹲下身,轻轻抱住他:“我会回来的。而且,下次带来更多的书,更多的灯。”
归途中,她写下第一份《边地实录》,共十三章,详述教育断层、医疗荒芜、司法腐败诸状。这份报告经周延转呈天子,引发朝堂震动。皇帝当场下令:三年内,全国偏远地区增设夜读堂一千二百所,派遣教师三千名,配备巡回医馆五十辆,并设立“基层正义基金”,专供贫民诉讼之用。
与此同时,一场悄无声息的思想战正在展开。江东士族虽表面顺从,暗中却扶持一批“新清谈派”,鼓吹“文不必载道,学当避世”,试图以风雅之名消解新政根基。他们在书院讲授庄老玄言,贬斥《治理律》为“俗务之书”,称李知微为“市井婆子”,谓陈阿六“粗鄙不堪”。
这场较量最终在太学爆发。一名寒门学子在辩论会上质问博士:“先生日日谈‘逍遥游’,可知北方孩童因无医而死?您说‘无为而治’,可曾见百姓因冤不得申而投河?”博士怒斥其“以下犯上”,将其逐出学堂。
消息传出,全国哗然。十七省夜读堂联合罢课一日,学生集体抄写《治理律》并寄往建康,信封上统一写着:“我们要的不是玄谈,是活路。”
天子震怒,亲临太学训诫诸生:“昔者王衍公弃清谈而入田垄,袁熙舍仕途而救饥民,李知微抱病批奏至最后一息。尔等读圣贤书,却不识仁义为何物,反以空言误国,岂非辱没先贤?”
随即下诏:自即年起,太学课程必须包含《民生实务》《法律实践》《灾害管理》三科,不及格者不得参加科举。同时恢复“耕读轮训制”:所有候选官员须在乡村服务满一年,方可授职。
十年之后,阿禾已成为西北道监察御史。她主持编纂的《边民权益保障法》正式颁行,明确规定:任何阻碍儿童入学、剥夺病人就医、隐瞒土地纠纷的行为,均属刑事犯罪。她还推动设立“儿童评议庭”,允许十岁以上孩童参与社区事务讨论,其意见具有法定参考效力。
某年春分,她重返莲塘里。村口石碑前,新一代孩童正在宣誓。她默默伫立,听着那熟悉的诵读声:
“凡民有地者,当以工养之;无地者,可申领公田,三年免税……”
声音清越,如溪流穿林。
仪式结束后,一个小女孩跑过来,仰头问:“阿姨,你是阿禾姐姐吗?老师说你就是那个带着灯走过沙漠的人。”
阿禾蹲下身,微笑:“是啊,我回来了。”
“那你还会走吗?”
她望向远方,麦浪翻滚,一如记忆中的初春。良久,她轻声说:“会的。只要还有地方看不见光,我就还得走。”
小女孩想了想,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工刻的木牌,上面画着一个圆圆的太阳。她郑重地放进阿禾掌心:“这是我给你的评分。满分。”
阿禾握紧木牌,泪水悄然滑落。
风又起了。纸鸢再次升空,那只燕子越过学堂屋顶,飞向湛蓝的天际。远处,新的队伍正整装待发,旗帜上写着六个大字:
“火种不灭,薪传万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