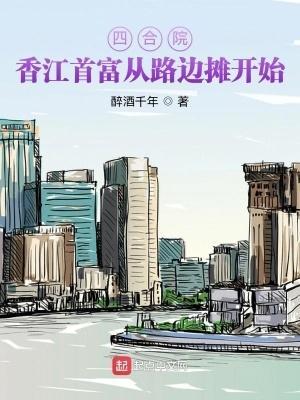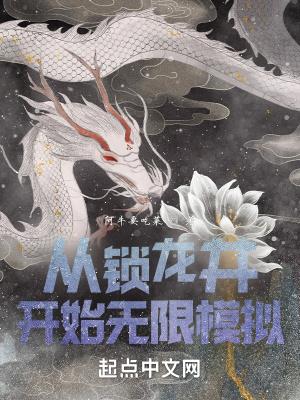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为变法,我视死如归 > 第247章 王小仙 你们俩都做参相公吧(第3页)
第247章 王小仙 你们俩都做参相公吧(第3页)
他怔住,良久不语。
宋玉在一旁轻声道:“这是城南孩童们新编的歌谣,已在坊间流传多日。”
王小仙仰望明月,眼角湿润。
他知道,文字可以篡改,史书可以粉饰,但人心不会。当一个母亲愿意让孩子不再拜官老爷,而是敬仰一名修堤的匠人时,这个国家就已经变了。
四月十五,女真使者抵达汴京。
阿骨打亲笔书信,言已整合各部,设立“勃极烈会议”,推行土地均分、废除奴隶制,仿宋制设“农政司”“军械局”,并愿以皮毛、人参、战马,换取农具、书籍、医师。
信末写道:“吾辈生于寒土,长于铁血,今始知,强国之道,不在弯弓射雕,而在使妇孺免饥、老弱得养。愿与大国结兄弟之盟,共抗天灾人祸,不以兵戎相见。”
王小仙回信曰:“善。愿两国如松柏共生,不争阳光,但护山林。”
五月,黄河上游第一座“松脂炸山工程”竣工。巨岩崩裂,河道疏通,新增良田八千顷。沿岸百姓立碑纪念,称此役为“开天渠”。
六月,泉州“匠学院”首届毕业典礼举行。百名学子披红挂彩,其中有党项少年达瓦之弟桑吉,以“改良风力磨坊”获头奖。王小仙亲授证书,问他志向。
桑吉朗声道:“我要回故乡建十座水车,让每条河都唱歌!”
全场掌声雷动。
秋七月,长安爆发瘟疫。王小仙急调“惠民医队”三十支,携《防疫手册》奔赴各地。书中载有隔离之法、草药配方、井水消毒术,皆通俗易懂。又令工匠批量生产“蒸馏净水器”,以陶罐、竹管制成,每户一件。
疫情三月而止,死者不足往年十分之一。百姓焚香祷告,称王小仙为“活菩萨”。
冬十月,赵顼下诏:“自明年始,全国推行《惠民册》普及工程,每村设‘识字角’,每乡配‘劝农匠’,每州建‘技学堂’。凡九年之内,务使天下无盲童,无荒田,无不通之渠。”
诏书传至边陲,戍卒含泪传抄;送达海岛,渔民悬于船头。
腊月三十,除夕。
王小仙未入宫赴宴,而是留在家中,与老母共度。其母年逾八十,双目已昏,然每日必问:“今日可有人饿死?”
儿媳答:“没有,官府送米到户,连最远的山沟都去了。”
老人点头:“那就好。你爹活着时常说,做官不为民,不如灶下狗。”
夜半,王小仙独自登上宅后小丘,遥望京城万家灯火。雪落无声,星河璀璨。
他轻声自语:“娘,我没让您失望。”
远处,不知哪家孩童点燃了一枚小型“鸣雷弹”,砰然一声,火花四溅,映亮半片夜空。
紧接着,第二声、第三声接连响起,此起彼伏,如同春雷滚动。
他知道,那不是军械,是百姓过年时自制的“欢岁炮”,依照公开的简易配方所造,无杀伤力,只为驱邪迎新。
笑声、欢呼声穿透风雪,洒满大地。
他站在那里,久久不动。
这一刻,他不再是那个被万人唾骂的“拗相公”,也不是权倾朝野的宰辅,他只是一个看见春天到来的普通人。
而春天,正从泥土里钻出,从孩童口中唱出,从每一座点亮的屋檐下流出。
他知道,变革早已超越了他的生命。
它活在每一个不愿再做饿殍的人心中,活在每一把用来开田而非杀人的铁犁之上,活在那一声声不再恐惧、只为喜悦而鸣的炮响之中。
薪火相传,不在一时一地,而在亿万人日复一日的选择。
他转身下山,脚步轻快。
新的一年,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