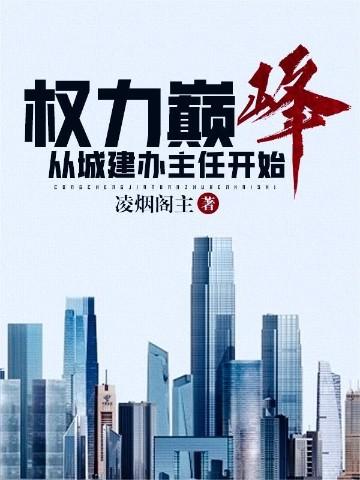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没有奥特曼?我将以怪兽形态出击 > 第二百三十五章 真正的迪迦现身圆谷初代海帕真理特利迦(第1页)
第二百三十五章 真正的迪迦现身圆谷初代海帕真理特利迦(第1页)
金色的光芒冲天而起,复合型的特利迦出现!
五十余米的身高在这个世界是极具冲击力的,但可惜。
千米加坦盘踞,让他这个巨人都显得渺小!
二者摆起战斗姿势,风声肃杀!
“出现在现实的。。。
林御拉悬浮于光网中央,十二道灯塔光束如经脉般缠绕他的身躯,将他与整座城市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共振体。他的意识不再局限于肉体,而是扩散成一张无形的网,覆盖每一寸被记忆浸染的土地。他能听见地下水管中流淌的旧日对话残片,能感知地铁站台砖缝里嵌着的某位母亲二十年前落下的泪滴频率,甚至能捕捉到风穿过废弃电话亭时发出的、类似叹息的震颤。
他成了活的记忆接收器。
可这能力并非没有代价。每当一段遗失的记忆涌入脑海,他就必须完整地体验一次那场情感风暴??不是旁观,而是亲历。一位老人临终前未能说出的遗言会让他喉头哽咽得无法呼吸;一场未完成的婚礼上新娘独自摘下头纱的画面则令他心脏骤缩,仿佛自己正是那个被命运夺走幸福的人。这些情绪像潮水般反复冲刷他的神经堤坝,而他知道,这只是开始。
“你还撑得住吗?”博也的声音从通讯频道传来,带着压抑的焦虑,“生理监测显示你的心跳频率已经偏离正常值%,脑电波呈现持续高幅震荡状态。”
“我还活着。”林御拉低声回应,声音在空中留下淡淡的回音轨迹,“这就够了。”
露西亚站在钟楼下仰望着他,手中紧握着一枚破损的记忆芯片??那是她在清理七十三号避难所遗址时找到的,里面存有最后那段童谣录音的残片。她本想等林御拉清醒后再交给他,但现在,她忽然意识到,他已经不需要“听”了。他本身就是那段歌声的载体。
“你会回来吗?”她问,声音很轻,却穿透了清晨微凉的空气。
林御拉低头看她,目光穿越层层叠叠的记忆雾霭,落在她脸上那一道细小的伤疤上??那是三年前静默层崩塌当晚,她为救一个被困孩童而留下的。那一刻,他不仅看到了她的现在,也“读”到了她从未说出口的恐惧:怕有一天,他会彻底消失在这无尽的记忆洪流中,再也找不到归途。
“我会回来。”他说,“只要还有人记得我。”
话音落下,他的身影缓缓分裂。一道虚影向北而去,直指欧亚大陆边缘一座早已荒废的边境小镇,那里曾发生过一场被官方抹去的大规模疏散事件;另一道则南下太平洋深处,追踪一段沉没于海底电缆中的集体梦境信号;而主意识,则朝着城市西侧一片被称为“遗忘带”的区域进发。
那里,有一座从未点亮的灯塔。
---
纪念之城西区,原名“归思区”,曾是战后安置难民的核心枢纽。但在二十年前的一次系统清洗中,整个区域的记忆数据被标记为“冗余信息”并强制删除,居民被迫迁离,街道封存,连地图上都再找不到它的名字。如今,这里只剩下空荡的楼宇、锈蚀的长椅和爬满藤蔓的公交站牌,像一座被时间遗弃的坟场。
然而,当林御拉踏入这片土地时,他的身体猛然一震。
无数低语在他颅内炸开。
“妈妈……冷……”
“别松手!求你别松手!”
“他们说新家有暖气……可为什么我们要走?”
这些声音不属于任何已知频段,它们像是从地底深处渗出的哀鸣,混杂着哭喊、咳嗽、脚步拖行的摩擦声,构成一首永不停歇的安魂曲。更诡异的是,空气中浮现出半透明的人影??模糊、残缺,如同老式电视雪花屏中闪现的画面。他们重复着生前的动作:排队领粥、抱着孩子奔跑、跪在地上翻找掉落的照片……
这是典型的记忆淤积现象。
但不同于普通遗失记忆的零散片段,这里的每一道影像都带有强烈的执念烙印,仿佛某种群体性的创伤在此处凝固成了实体。
林御拉闭上眼,主动打开神经通道。
刹那间,洪水决堤。
他看见雪夜中的难民营,帐篷接连倒塌,婴儿啼哭声淹没在暴风呼啸里;看见医疗队因资源不足只能选择救治对象,一名医生含泪签下放弃名单的手在颤抖;看见一群孩子围坐在火堆旁,用炭笔在纸上画出各自梦想的家园,第二天却发现其中三人已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……
而最深处的记忆核心,是一扇门。
一扇由数百张人脸拼接而成的巨大铁门,每张脸都在无声呐喊,双眼空洞,嘴唇微启,似在祈求什么。门后传来沉重的撞击声,一下又一下,节奏稳定,如同心跳。
“你想进去吗?”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。
林御拉睁开眼,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不远处,约莫七八岁,穿着一件褪色的红毛衣,脚上是一双明显不合尺寸的大雨靴。她手里抱着一本湿漉漉的图画册,封面写着:“我的家。”
“你是谁?”他问。
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孩子。”她说,“大人们都说这里没人了,可我知道,我们都没走。我们只是……被忘了。”
林御拉蹲下身,平视她的眼睛:“那扇门后面是什么?”
“是我们不肯闭眼的理由。”小女孩抬起头,目光清澈得近乎残酷,“那天晚上,政府说要转移所有人去安全区,可车不够。他们让我们抽签。我和妹妹抽中了号码,可妈妈把她的名额给了我,自己留了下来。后来雪崩来了,整条街都被埋了。他们说没人幸存。可我们都还在。我们一直在这里,等着有人来告诉我们??你们没有被抛弃。”
泪水顺着林御拉的脸颊滑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