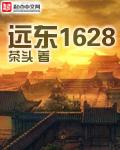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捉妖 > 第703章 你在京城有什么仇家(第2页)
第703章 你在京城有什么仇家(第2页)
北漠军营,士兵们在风雪中听见鼓声,循声而去,发现一座埋于沙下的青铜鼓,鼓面绘有人脸,双目微睁,似在等待。
这些现象只有一个共通点:它们都不是人为传播,而是自发觉醒。
记忆,正在回归。
而在这股浪潮中心,陆鸣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彻底断裂了??那是多年来强撑的责任,是背负使命的枷锁。他不再是“守灯人”,也不再是象征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,一个愿意记住、也敢于遗忘的人。
他缓缓跪下,将残笛放入灯前。
“我不再唱了。”他说,“该你们了。”
话音落下,蓝焰骤然转白,继而化作金色火焰,腾空而起,在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符号??九鼎合一之形,下方缀着八道波纹,第九道则断裂未续。
这是召唤。
不是命令,不是号令,而是一种邀请。
三日后,第一人响应。
是个哑巴少年,生于静语城,从小被禁止发声。他在梦中听见母亲的声音,醒来后扑到音坛石碑前,用手指蘸血写下:“我想说话。”
当晚,他站在海边,张开嘴,发出人生第一个音节。不成调,不悦耳,甚至撕裂喉咙,流下鲜血。但那一声呜咽,竟引动海底灯焰再次跃动。
第四日,一对夫妻带着失忆的父亲来到启音城。老人已不认识儿女,只会机械重复一句话:“别吵,安静才好。”可在听到街头孩童清唱《唤心曲》时,他忽然停下,嘴唇微动,接着放声大哭:“娘……我想家了……”
第五日,前巡使团成员现身。那个曾奉命追杀他们的玄袍人,如今披着粗布衣裳,跪在石台前,双手捧着断裂的玉箫:“我杀了太多‘记得’的人。现在,请让我学着听一次。”
越来越多的人来了。
他们中有曾信奉“净魂即秩序”的道士,有因失去至亲而拒绝回忆的寡妇,有从小被教育“情感是弱点”的武修子弟……他们不求宽恕,只求一听。
陆鸣每日坐在桃树下,不再言语,只是静静看着这些人围灯而坐,或哭或笑,或嘶吼或低吟。他知道,这场战争从未结束,也不会真正胜利。因为只要人类还惧怕痛苦,遗忘就会卷土重来。
但他也知道,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开口,哪怕声音微弱,哪怕走调跑拍,灯就还在。
直到某个雪夜,一个小女孩爬上他的门槛,怀里抱着一把破旧的铃鼓。
“爷爷说,你是第一个唱歌的孩子。”她仰头望着他,眼睛明亮,“我现在也是了。我能在这里唱吗?”
陆鸣点点头。
她于是盘腿坐下,轻轻摇动铃鼓,哼起一首稚嫩的歌。旋律歪歪扭扭,却是完整的《唤心曲》第一段。
风穿窗入,吹动檐角铜铃,应和着她的歌声。
远处,归墟海面泛起淡淡金光,仿佛回应。
陆鸣闭上眼,嘴角浮现笑意。
他知道,这不是终点。
这是又一次开始。
许多年后,当新一代的孩子们问起:“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唱歌?”
老师会指着课本上的图画讲述:
“因为在很久以前,世界差点忘了如何哭泣,如何欢笑,如何爱人。
有一个叫陆鸣的人,他不愿意忘记。
所以他开始唱歌。
然后,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。”
而在无人知晓的深海之下,那盏蓝焰灯依旧静静燃烧。
它的光芒不足以照亮整个海底,却始终稳定跳动,像一颗不肯死去的心脏。
每当风起云涌,暗流涌动,它便会轻轻闪烁一下,像是在问:
“你还记得吗?”
答案,总会在某一扇窗后响起。
或许是一段笛声,或许是一句童谣,或许仅仅是一个人,在夜深人静时,对着星空轻轻哼唱:
“月儿弯,灯儿亮,娘亲守你到天光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