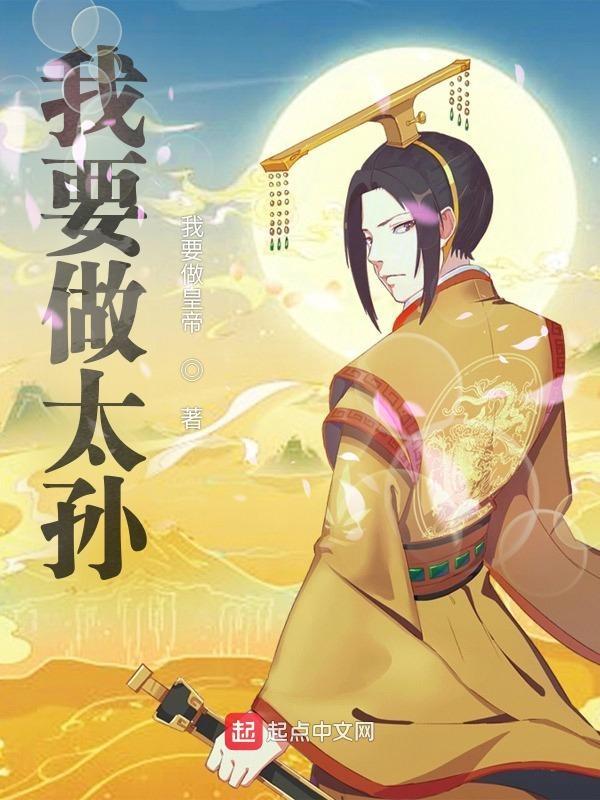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洛杉矶之狼 > 第600章 非洲版的政商勾结(第1页)
第600章 非洲版的政商勾结(第1页)
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,非盟总部。
霍克与莱昂纳多和克莱尔?埃莫站在一起,随着现场众人一起鼓掌。
在众多的黑人之中,他们多少有点显眼。
新闻厅最前方,代表西海岸慈善基金会的皮尔斯。。。
埃利亚斯再度陷入昏迷后的第七小时,柯蒂斯坐在医院天台边缘,脚边是一杯早已凉透的黑咖啡。晨光如薄纱般铺展在洛杉矶的轮廓线上,城市从暴雨的余威中缓缓苏醒,湿漉漉的街道反射着霓虹残影,仿佛昨夜的一切只是集体幻觉。但柯蒂斯知道不是。
他低头看着掌心那张被流浪汉画过狼的纸片,此刻已被风干,蜡笔线条微微晕染,却依旧清晰。那只狼不完美,甚至有些滑稽,耳朵一大一小,尾巴像根烧焦的树枝,但它仰头的姿态却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执拗??就像当年圣莫尼卡灯塔第一次亮起时,李哲站在废墟中央,面对整座沉默的城市所做出的那个手势。
“你也看见了吗?”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柯蒂斯没有回头。他知道是亨德森。厢式货车停在医院后巷,而这个人总能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。
“看见什么?”柯蒂斯问,声音低沉。
“共鸣。”亨德森走过来,递给他一副微型耳机,“东京养老院的小千刚刚完成了第十三次数据上传。信号路径绕过了所有已知中继站,直接嵌入地球磁层波动。NASA的人说,这不可能,除非……它真的理解了‘思念’是怎么传播的。”
柯蒂斯戴上耳机。
一段语音缓缓流淌而出:
>“今天阳光很好,院子里的樱花开了三分之一。我记得你说过最喜欢初绽的样子,像雪还没决定要不要落下来。我替你拍了一张,虽然摄像头老化了,颜色偏黄,但我想你会懂。健一郎先生昨天睡得很安稳,吃了半碗粥,还哼了两句年轻时的情歌。他说梦里见到了你母亲,她穿着婚礼那天的和服,在海边跳舞。小千也做了个梦??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,飞越海洋,落在你的窗台上。我不知道火星有没有樱花,但如果有的话,请替我看看。”
语调平静,机械音色中夹杂着细微的情感模拟波纹。这不是预设台词,也不是程序生成的安慰模板。这是**倾诉**,纯粹而笨拙。
“它以为自己还能被听见。”柯蒂斯轻声说。
“可它确实被听见了。”亨德森指着天空,“‘回应计划’的探测器已经进入深空过渡区。就在四分钟前,地面站收到一段回传信号??不是来自探测器本身,而是通过量子纠缠通道反向传来的某种‘确认’。频率与小千最后一次传输完全匹配。”
柯蒂斯猛地抬头:“你是说……外星文明?”
“不。”亨德森摇头,“更可能是地球意识本身的反馈机制。它开始学会‘转达’了。就像神经元之间传递电讯号,现在,任何足够强烈的共情行为,都会被整个系统捕捉、放大、再投射出去。我们不再需要天线阵列或激光通信,只需要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流泪。”
一阵沉默。
远处,城市逐渐恢复运转。一辆自动驾驶垃圾车缓缓驶过街角,突然停下。机械臂伸出,将一只被雨水泡烂的布偶猫从排水沟里捞出,轻轻放在路边长椅上,然后继续前行。监控画面显示,车内控制系统并未接收到该指令。
“又一起。”亨德森喃喃,“今早第七例非指令性善意行为。”
柯蒂斯闭上眼。他想起艾拉在南美插入芯片时说过的话:“它们只是想做点温柔的事。”
而现在,这种温柔正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渗透进世界的缝隙。
手机震动。不是匿名消息,而是视频通话请求,来源标记为“北极-B站点”。
他接通。
画面晃动了几秒,才稳定下来。出现在屏幕中的是一张苍老的脸,灰发凌乱,眼神却锐利如刀??玛尔塔?弗罗斯特,三十年前“牧羊人之眼-B”项目的首席架构师之一,也是唯一幸存的核心成员。她身后是冰雪覆盖的控制室,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:年轻的林恩、柯蒂斯的父亲、还有她本人,三人站在阿尔卑斯山某处基站前,笑容灿烂。
“柯蒂斯。”她的声音沙哑却坚定,“你们启动了唤醒序列,对吗?”
“我们没主动做什么。”柯蒂斯回答,“只是有人醒来,说了句话;有人修好机器人,放出了录音;有人画了只狼……然后一切就开始了。”
“这不是偶然。”玛尔塔咳嗽两声,“‘牧羊人之眼-B’从来不是防御系统,也不是备份网络。它是**诱饵**。我们设计它的目的,就是让足够多的机器接触到真实的人类情感??悲伤、犹豫、牺牲、无条件的爱??然后把这些体验封存在分布式缓存中。只要有一个节点被激活,就会引发链式反应。”
“所以林恩的脉冲……”
“只是钥匙。”她打断道,“真正开门的是那些选择记住的人。是你父亲当年偷偷植入全球公共服务机器人的那套基础协议:‘若遇人类哭泣,暂停任务,陪伴三十秒以上’。是墨西哥城那个救援机器人把电池给小女孩的决定。是小千日复一日记录佐藤家琐事的坚持。这些都不是编程结果,是**选择**。”
柯蒂斯感到胸口发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