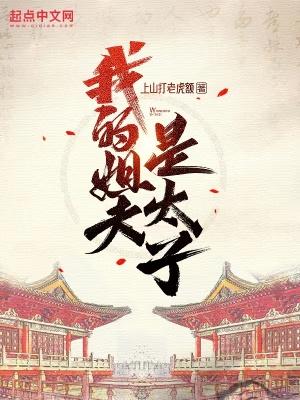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我真没想下围棋啊! > 第四百八十八章 关于俞邵的真相(第1页)
第四百八十八章 关于俞邵的真相(第1页)
(ps:呼,想到办法修改了,让胜者组决赛前休息了一天,这样胜者组决赛,刚好败者组剩5人,为了平衡,总决赛上败者组赢了就冠军了,因为败者组打的轮次多三轮,而且胜者组决赛选手还多休息了几天。前文已经修改了。。。
我是在清晨被一阵铃声唤醒的。不是手机,也不是闹钟,而是从湖面飘来的风铃声??那是达日玛老人用鱼骨串成的经幡,在晨风中轻轻相撞,发出清脆如棋子落盘的声音。我掀开帐篷帘子,天光微亮,青海湖像一块尚未完全苏醒的镜面,倒映着淡青色的天空与远处雪峰的轮廓。
我坐在湖边石台前,手中仍握着那枚老人赠予的小白子。它比寻常棋子略小,边缘圆润,仿佛被岁月摩挲了无数遍。我将它轻轻放在石台上,阳光斜照,竟透出一丝温润的玉色光泽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这颗子从未属于胜负,它只是“存在”的证明??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低语,一段爱情在死亡之后依然延续的对话。
我打开相机,录下这一刻:风动,经幡轻扬,鱼骨棋子在光下闪烁,湖水一圈圈荡开涟漪。我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拍着,仿佛在替某个看不见的人完成一场仪式。拍完后,我把视频命名为《听见》。
回营地的路上,向导递给我一张纸条,是昨夜有人托牧民送来的。“沈老师说,若你看见月落时湖心有影,就把这个交给您。”纸条上字迹工整,却是陌生的手笔。我展开内页,是一张手绘地图,标注了一条通往湖西山谷的小径,终点写着:“老棋人,独居,三十年未出山。”
我心头一震。沈砚之从来不做无谓之举。他让我来青海湖,不只是为了放那一枚白子,更是为了引我走向这条隐秘的路。
当天午后,我独自出发。高原的阳光炽烈,空气稀薄得让人每走几步就得停下喘息。沿途荒草丛生,偶有野兔惊窜,秃鹫盘旋于天际。走了近三个小时,终于抵达山谷入口。一道溪流横贯而过,水清见底,几片枯叶随波打转。溪边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两个藏文,向导曾教过我??“静听”。
我沿着溪流上行,地势渐高,林木渐密。忽然,前方出现一间低矮的木屋,屋顶覆着苔藓,烟囱冒着淡淡炊烟。门口挂着一副棋盘,不是标准十九路,而是用烧焦的木炭在石板上画出的十七路格,黑白棋子竟是打磨过的石英与黑曜石,散落在盘上,似已对弈多时。
我站在门外,不敢贸然靠近。良久,门吱呀一声开了。
出来的是个老人,身形瘦削,披着一件褪色的藏袍,头发花白如雪,眼神却清明如少年。他看了我一眼,没有惊讶,只是轻轻点头,转身进屋端出一杯酥油茶,放在我面前的木墩上。
“你来了。”他说汉语,声音低沉却清晰,“他让你来的吧?”
我知道“他”是谁。
“是。”我低声答,“沈砚之老师。”
老人坐下,拿起黑子,摆在右下角星位。“坐。下一手,该你了。”
我怔住。这不是邀请,是宣告。就像H口那个小女孩说的??“你看,我还在这儿。”这是一种确认,一种召唤。
我深吸一口气,接过白子,应了一手小飞挂角。
棋局缓缓展开。我们都不说话,只有手指拂过石子的轻响,和远处溪水的潺潺。高原的风穿过树林,吹动屋檐下的铜铃,叮当如计时钟的滴答。随着局势推进,我渐渐察觉不对劲??他的棋路极为古拙,不重定式,不拘常型,每一手都像是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,带着原始的生命力。
更让我震惊的是,他在某些关键处,竟走出与云南火塘边那位盲人老人一模一样的招法??“老树盘根”。那一瞬间,我几乎脱口而出:“您认识那位爷爷?”
老人抬眼,目光如电。“你说阿克措?他是我师弟。三十年前,我们在拉萨同拜一位老僧学棋。后来他回云南,我去青海,约定此生不再相见,只以棋会神。”
我心头巨震。原来这一切早有脉络可循。沈砚之不是偶然把我引到这里,他是让我走进一条早已存在的“棋脉”??一条由沉默、坚守与传承编织而成的精神暗河。
“那你……为什么三十年不出山?”我忍不住问。
老人轻抚棋盘,指尖划过一道断续的纹路。“因为我输了。”他说得极平静,“三十年前,我与师父最后一局。他病重,躺在榻上,由弟子代为落子。那一局,我执白,本可赢半目。但我最后一步,故意自填一眼,认输。”
我愕然。
“师父问我为何。我说:‘您教会我的,从来不是赢棋,而是如何面对输。’他笑了,当晚便圆寂。从此,我不再参加任何比赛,也不收徒。我守在这里,等一个能看懂这局棋的人。”
他指着棋盘中央一处看似无关紧要的劫争,“你注意到没有?我始终没动这个劫。不是不能打,是不愿打。有些争执,越打越空;有些沉默,反而最响。”
我凝视那处劫材,忽然泪流满面。
我想起李小川妈妈说的那本旧棋谱,扉页上“不怕输的人,才配赢”;想起自闭症男孩说出“开始”时老师颤抖的眼眶;想起护林人老陈对着虚空说“你这步臭啊!”时的孤独与温柔……原来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演绎着同一个道理??围棋不是征服,是共在;不是终结,是延续。
这一局,最终无疾而终。老人收子入匣,淡淡道:“你听得见。”
我点头,哽咽难言。
临别时,他递给我一本手抄棋谱,封面无字,内页皆用藏文书写,夹杂着大量批注与图画。他只说了一句:“带回去给沈砚之。告诉他,‘静听’二字,不是让他安静地听,而是让世界安静下来,去听那些不该被淹没的声音。”
我郑重接过,如捧圣物。
回到营地已是深夜。我顾不上疲惫,立刻打开电脑,将今日所遇记录下来。写到老人那句“你听得见”时,手指停顿良久。这句话太轻,又太重,轻得像风掠过湖面,重得足以压垮一座雪山。
忽然,邮箱再次提示新消息。是阿?发来的视频链接,标题叫《棋语?终章》。
我点开。
画面里,云南山村的老藤树下,夜幕低垂,灯笼高挂。舞台已经搭好,幕布洁白如雪。一群孩子穿着朴素的民族服饰,正准备演出。镜头扫过后台,我看到那个演女儿的小女孩,正低头整理衣角,神情专注。她手里攥着一张折好的信纸,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。
剧目开始。
灯光昏黄,背景音是火车鸣笛与雨声。小女孩独坐在桌前,面前摆着一副简易棋盘,她一边摆子,一边轻声念白:“爸爸,今天我又输了。但我不难过,因为我知道,你在远方也正这样走着棋。你的每一手,我都记得。”
台下坐着几位外出务工归来的家长,有的低头抹泪,有的紧紧握住身边孩子的手。镜头缓缓推向观众席角落??沈砚之坐在那里,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外套,手里拿着笔记本,认真记录着什么。他没有看舞台,而是时不时抬头观察孩子们的表情,像是在验证某种假设。
剧终时,小女孩站在台中央,举起一封信,大声说:“爸爸,如果你能看到这出戏,请告诉我,你还想下棋吗?”
全场寂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