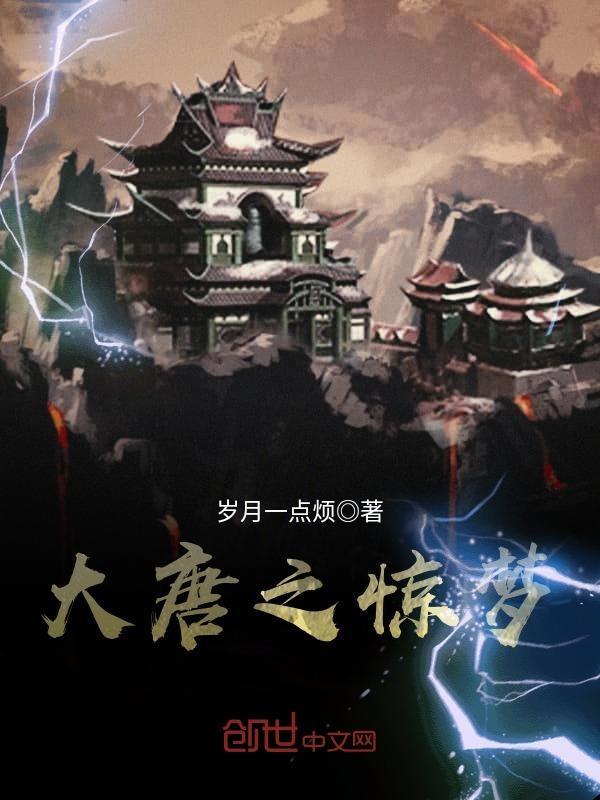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> 第663章首都之行的差池(第2页)
第663章首都之行的差池(第2页)
亲情的链条,在一句摇篮曲中断裂多年后,竟被一段音频重新接上。
江辰站在绥芬河口岸的桥头,望着界河上漂浮的碎冰,忽然意识到:“萤火”之所以能点燃人心,不是因为它多先进,而是它允许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??声音、图画、方言、梦境??去表达那些无法被标准化测量的痛与爱。
返程途中,列车停靠长春站。江辰接到林晚晴的电话。
“数字遗言信箱”上线两个月,已有十二万人创建账户。其中三千二百余人设置了触发条件并完成最终发送。最新一条自动推送的信息来自甘肃定西,收件人是陈建国(教师)的儿子。
内容只有短短一句:“儿子,爸今天学会说‘我爱你’了。虽然你听不见,但我必须说。”
发送时间,正是男孩忌日当天凌晨五点十七分。
江辰握着手机,久久说不出话。
他知道,这不是技术的胜利,而是一次迟到的救赎。
沈阳站的最后一场活动安排在一处老旧社区中心。这里是“家长倾听训练营”的试点区域,已有两百多位父母完成课程。江辰原计划只是观摩,却被临时推上台分享经验。
台下坐着七八十位中年男女,多数穿着朴素,有些人手里还捏着记事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笔记。
主持人介绍完毕,一位母亲站起来提问:“江老师,我家孩子高三了,成绩一直上不去。我每次问他学习情况,他就摔门。我不是不理解他,可我也快崩溃了,怎么办?”
江辰想了想,反问:“您最后一次认真看他眼睛说话,是什么时候?”
女人愣住。
他又问:“您有没有试过不说‘你该怎样’,而是说‘我担心你’?”
全场寂静。
片刻后,另一个父亲低声说:“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听孩子说话,是我自己不敢说真话。我失业半年了,瞒着全家。每天假装上班,其实就在公园长椅上坐一天。”
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湖心,激起层层涟漪。
陆续有人开口:有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不敢告诉家人,怕被说“矫情”;有人说夫妻十年没好好聊过天,只剩下“饭做好了”“水电费交了”;还有人坦白,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拥抱过父母。
江辰拿出随身携带的“情绪卡片”,让每人抽取一张,上面写着不同情绪词:羞耻、无助、委屈、恐惧、孤独……
“现在,请用这个词造句,主语必须是‘我’。”
“我感到羞耻,因为我不能给女儿更好的生活。”
“我感到无助,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哭了一整晚的妻子。”
“我感到孤独,因为我妈去世后,家里再没人叫我乳名。”
声音此起彼伏,像是压抑多年的地下水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活动结束时,已是深夜。江辰独自走在回酒店的路上,寒风吹得路灯摇晃。手机震动,是林晚晴发来的消息:
【“萤火列车”设计方案通过初审。发改委建议增加少数民族语言支持模块,并考虑冬季供暖问题。】
他回复:【告诉他们,我们会配上暖光灯带,也会请懂蒙语、藏语、维吾尔语的人同行。只要有人愿意说,我们就一定听得见。】
抬头望去,城市灯火通明,可他知道,真正的黑暗不在夜里,而在无数亮着灯却无人交谈的房间里。
回到北京那天,项目组召开闭门会议。有人提出担忧:“列车运行成本太高,三年内很难盈利。”
江辰平静地说:“我们从没打算盈利。‘萤火’的意义,从来不是赚多少钱,而是让多少人在黑夜里看见光。”
最终,“萤火列车”获批为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工程,首列车将于春季正式启航。车身涂装采用渐变萤黄色,车头印着一行字:“这里不说正确的话,只说真心的话。”
发车仪式当天,江辰邀请了马小兰、周涛、次仁卓玛以及几位曾在平台上发声的普通人共同剪彩。孩子们带来了亲手绘制的愿望卡,贴满车厢内壁。一位曾在“失败博物馆”留言的老兵,执意将自己的勋章挂在“声音博物馆”展柜上,说:“比我更值得被记住的,是那些没机会说话的人。”
列车缓缓驶出站台,汽笛长鸣。
江辰站在月台上,看着它远去,忽然收到一条系统通知:
【用户“云边的小羊”已连续登录七日,今日发布新动态:今天我和阿妈一起采了格桑花,广播里的铃铛声,真的响了。】
他笑了,眼角泛起细纹。
春天来了。
山河依旧辽阔,人间仍有沉默,但总有些声音,正在穿过风雪,抵达另一颗等待被听见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