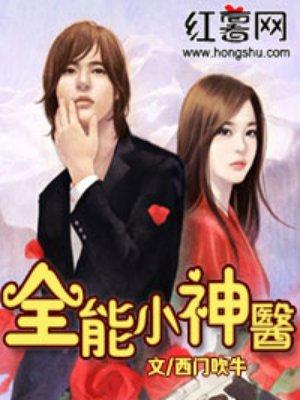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我也没想都养黑化来着 > 045风波恶四(第3页)
045风波恶四(第3页)
完全没有适应过来。
陆洄从小是个散养的世子,身边其实一直没有真正贴身的下人,后来病得起不来床,到了不得不有人的地步,就是萧璁笨手笨脚地从头一点点学起,时间长了已成习惯。
可一旦有“跟在我后头端茶倒水的是个有鼻子有眼的成年男人”这种念头,一切就迥然不同。萧璁小时候踮着脚给他添衣梳头尚算好玩,夜里不老实的时候抱着他喂药暖床也属孝顺,现在顶着这副体格做这些事像什么话?
不管他在这怎么想,左右萧璁自己是没意识到的,陆洄每每从外头折腾回来,一进门总能第一眼看见萧璁的身影。
这人好像也不是在刻意等他,有时候是坐在案边看书,有时候是在廊下侍弄花或者猫,有时候只是拄在小榻边闭目养神,却总能让人一回身就发现,再用那双要了命的绿眼珠子轻飘飘看来一眼。
好像他是自己在外头藏的什么秀色,本来是精怪化成的,你不看他时是静默姝丽的花花草草,什么时候一搭眼再一定睛,霎时是个望穿秋水等了不知道多久的幽怨美人。
……还是个素服披发,衣衫不整的鬼美人。
这感觉属实瘆人——悚得陆洄接茶都呛了一口,接着咳了个昏天暗地。
“慢点,”萧璁给他顺气,“咳了好些天都不见好,明天别出门了。”
陆洄感觉到他手心的温度,心神不宁地把茶喝了,罕见小心地思索着:他已经有天魔引的心结,本来就容易多想,得想个办法一点点说开……
“你想主动去会会大长公主?”
陆洄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萧璁同他说话,又看了一眼桌上扔着的人皮面具:“当然不能就这样过去。我搭这条线,主要想探探皇帝的意思。”
时隔多年,这是萧璁头一次从他嘴里听见“皇帝”两个字,他不动声色垂下睫毛,问:“除了给玄察院和天枢阁换血,或者顺带借机杀杀陈氏的威风,还有什么?”
陆洄点点桌面:“江安的事传到燕都,皇帝‘闻之震怒,当堂任命镇国大长公主彻查’。震怒当然是逢场作戏,但是公主不是一般的刀……”
他低头重新去找茶杯,目光下意识避开萧璁敞开的领口:
“百仙会重启一事本来就难以捉摸。他不像先帝,不好这一口,甚至是有点忌惮玄门的,一旦动了,不可能轻拿轻放。”
萧璁不喜欢陆洄用“他”代指皇帝,把茶杯递过去,轻声道:“师父觉得陛下会怎么处置?”
“我不知道他知道什么。”陆洄疲倦地叹了口气,手扶在杯上,一时没动,“金鉴池与陈氏的勾结他肯定有数,但知道到什么程度?子夜歌的事呢?十二障大魔和圣女的事呢?”
至于更远的、十八年前宫中……
算了,皇帝知道这个干嘛?他喝口水,把剩下的话咽了。
“陛下知道什么暂且是公主来后才要想的事,我更关心的事……子夜歌想要什么。”
萧璁立刻又把茶水斟了七分满,之后缓缓在陆洄对面坐下,后者立刻避无可避地撞进那双认真的绿眼睛里。
这人遮住瞳色的幻术本来因为伤重力竭散去了,这几天不知道是忘了还是觉得两个人猫在别院里无所谓,竟然一直没补上。
他眉眼间距很近,总显得有点凶,只有这样对上才能发现眼尾其实是下垂的,睫毛又葳蕤,配上那双得天独厚的碧色眼珠,很容易给人一种……深情的错觉。
“有一点我一直很疑惑。“萧璁注意到对面人的迟疑,刻意把字音放得很低很轻,”谢前辈把我认成蓝珠,大部头是因为沧澜宫圣女一早说过自己还会重回地宫。那……子夜歌又为什么要再造一个涵云道人呢?”
“为什么?”陆洄顺着他的意思。
萧璁:“这是一群疯子,什么后果也不顾,什么代价也不吝惜,这比单纯牟利可怕得多,因为一般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逻辑,根本想不到他们想干嘛……除了他们的同类。”
“……”
陆洄直觉他下面不是什么好话,一瞬间有股恶气,脱口问道:“什么逻辑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