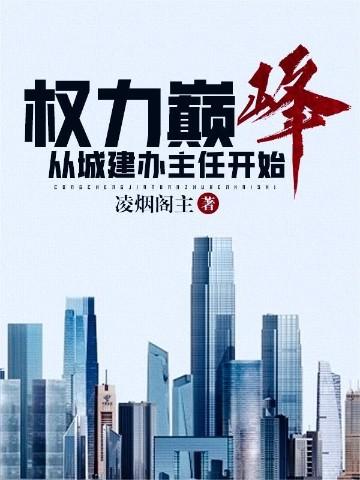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照破山河 > 第 56 章(第2页)
第 56 章(第2页)
顾来歌与他对视之间,眼底翻涌过一些伶舟洬读不懂的复杂情绪。只是他还来不及深究,便见顾来歌已然收敛了所有外露的情绪,只微微点了点头,不再多言。
重掌权柄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顾来歌需要时间,去重新熟悉这数月来堆积如山的政务脉络,更需要小心翼翼地,重新确立自己身为人君的绝对权威。
他很快发现,这次伶舟洬辅佐明显不同于往日,许多重要的决策在开始施行之时,效率极高,甚至远超他从前在位之时。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断过程,却早已在无形中绕过了他。
那些关乎钱粮调配、官员升黜、乃至边关守备的诸多事务,伶舟洬留下的印记无处不在。当顾来歌不可避免地看到那些刻意模仿自己笔迹、却终究在起承转合间透出不同气韵的朱批时,总会下意识地微微蹙眉。
少年人心高气傲,敢随手将一颗真心生生剜去,就敢再连同流出的烫血一并赠予眼前人。
但少年人又何等无知,眼前路尚不能看得太清,当然也不知道,承诺这种东西,往往潜伏在不知前路何处的年岁深处,等待着在某个始料未及的时刻,反噬其身。
顾来歌重新把握朝政这些时日,第一桩棘手的难题,在五月悄然而至,后记载于亳平志半苏卷事纪:
仲夏朔十有一日,亳平郡内半苏之地,有周、郎两姓大族因田垄界址之讼,积怨骤发。是日聚众持械相攻,血沃阡陌,伤毙者计三十有七,白幡蔽野,乡邑震动。
事闻天听,朝议纷纷。户部尚书伶舟洬力主强硬弹压,举荐兵部校尉孔仲聂前往镇抚。然孔生性刚愎,措置失宜,一味以武力威慑,反激其变,致使械斗愈炽,民怨沸腾。
消息传回,帝顾来歌闻奏,色未尝改,惟敛袖轻叹:“耕者争寸土而弃千粟,愚矣。”遂敕天策将军陆庭松持节赴之。
陆将军至,未以大军压境,反先令随行军士结营于五十里外,自己则单骑入两姓宗祠。他焚香告祖,剖陈利害,更以官仓余田补其不足,示以公道。又明察暗访,终擒获暗中煽风点火、意图趁乱牟利之凶徒三人,立斩于市,以正刑典。其余参与械斗者,则视情节轻重,或训诫,或薄惩,恩威并施。
两姓民众见其处事公允,手段果决,皆感其诚,遂解甲伏罪。旬日之间,犁重归垄,炊烟再起,半苏之地复归安宁。
帝闻捷报,于朝会之上,朱批曰:“能止戈于樽俎,胜破敌于疆场。陆卿深知民情,洞悉时务,朕心甚慰。”当即擢升陆庭松为镇国大将军,秩正二品,赐麟纹金甲,领京畿十二卫兵马,荣宠极盛。
而伶舟洬则自请罚俸半岁,以承担举荐不当之责。出乎众人意料,帝竟温言慰留,称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”,未加深究,朝野由此愈服圣君之量。
陆庭松不过二十七岁,便已官至二品,掌京畿重兵,这是莫大的荣宠。退朝之时,恭贺之声不绝于耳。
下朝后,伶舟洬穿过人群,走到陆庭松面前,脸上是无可挑剔的温和笑容,拱手道:"恭喜相礼,晋位镇国,实至名归。"
陆庭松看着他的笑容,心中却无多少喜悦,反而像是压了一块巨石。他沉默一瞬,才低声道:"却行,你……"
"经此一事,可见陛下已然圣心独断,洞察秋毫。"伶舟洬不着痕迹地打断了他,笑容依旧,声音平和,仿佛只是随口感慨,"你我身为人臣,能做的,便是恪尽职守,尽心辅佐。望将军日后,能善用此权,不负圣恩,亦不负……你我年少之志。"
伶舟洬此番话语得体周全,明明是挑不出半分错处,甚至带着与从前如出一辙的恳切与真挚。
但落入陆庭松耳中,却分明听见被他刻意咬重了的“身为人臣”四个字,还有那平和语气下,一丝难以言喻的紧绷。
陆庭松从前爱说些逗弄人的话,却似乎是从去年深秋起,就变得少了许多。明明此时圣眷正浓,却也没能抵消他眉间不知何时染上的那几分凝重。
他最终只是点了点头,将所有翻涌的情绪压下,沉声应道:"自然。谨记尚书大人之言。"
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喊“却行”二字。
“尚书大人”这个称呼分明带着刻意将人推远的疏离,但伶舟洬却毫无所察一般,只是微微一笑,也不再多言,转身融入散去的人群中。
伶舟洬独自一人走在宫道上。今日阳光很好,照在朱墙金瓦上,折出一道有些刺目的光。
在回廊尽头第一个转角,他脚步微顿,忽然瞥见东侧外,多了一棵不知何时栽种的海棠,此刻正大张旗鼓探过宫墙,好似胭脂泼过,烧尽一片暮色。
算算日子,恰好正是海棠该如火如荼的季节。他不禁一怔,微微眯起双眼,看晴光透过海棠枝叶的罅隙,忽然想起很多年前,也是这样的阳光落在灼灼海棠枝上,曾有三个少年,立誓要永不相负。
忽然一阵长风掠过,伶舟洬也在这时猛然醒过神来,眼前的海棠树却随他恢复清明时,逐渐消失不见。再定眼望去时,那里立着的,竟是一棵枯枝败叶的梧桐。
如今时节,分明该是窃荫常昼,昏蝉不知寒。为何会有孑然独守的将死梧桐呢?
他微不可察的皱了皱眉,转身欲走。有枯叶打着旋落在他衣摆旁,却被他一脚踩碎,没有片刻停留。